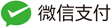高原的夜风撞在玻璃窗上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连队会议室里灯火通明,党员、团员围坐在会议桌前,党旗悬于墙上,那抹红色沉静肃穆,将整个空间映照得格外庄重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肃然,仿佛连高原稀薄的氧气也在此刻凝滞,等待一次灵魂深处的叩问。
“同志们,”指导员的声音沉稳, “不妨停下脚步,回头看一看。”他目光如炬,扫过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庞,“问问自己当初为何迈出那一步,站在党旗团旗下?”这声音不高,却如同撞钟,震得人心里一颤。
指导员的话音落下,党员王刚下意识地攥紧了搁在膝盖上的拳头,思绪猛地回到贵州莽莽群山。他是大山的孩子,家境贫困:父母多病,守着几亩坡地,曾是村里的五保户。他原以为自己会延续父辈的生活。直到那天,一群胸前别着党章的人,走进村子。他们在挨家挨户调研后说:“老乡,一起努力,这顶‘穷帽子’一定要摘掉!”其中一位干部将王刚家记为了重点帮扶对象。从此,他们成了常客:带来了优质种子,传授了先进技术;为王刚家办理了疾病补助和助学补助……年复一年,泥路硬化,土屋变砖房。终于,家庭年收入突破了三万,甩脱了“五保户”。永生难忘的是当接过大学录取书时,那干部满眼欣慰:“好小子,飞出大山!好好学,报效国家!”那一刻,昏黄灯下,他们胸前的党章,亮如启明星。大学里,怀揣这颗被点亮的初心,他毅然参军。此刻,回忆如潮,他喉结滚动,似要将那家乡巨变与胸前的光芒咽下,融入骨髓——追随那光,成为那光!
后排,李锐陷入了沉思。入团时那点朦胧的自豪,在指导员的话语中被层层剥开,露出了更深的内核——原来那不仅是荣誉,更是召唤。他抬起头,目光不由自主地越过战友们的肩头,落在那面鲜红的党旗上。内心深处在叩响:为什么入党?为了像班长那样,成为迷途暗夜里那盏引路的灯。这念头一起,仿佛有一束光穿透了高原的迷雾,直直地照进他年轻的心底。
随后的小组讨论,气氛陡然变得灼热,如同密闭的炉膛。灯光下,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绷紧了,记录本上的字迹越来越重,像刻上去一般。
“班长,”李锐的声音带着些许迟疑,“你训练要求没得说,严得很!可有时我们动作慢了点,你那个眉头一皱,眼神跟刀子似的,大伙儿心里都怵得慌……”王刚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他抬眼,迎上李锐的目光,沉默了几秒:“嗯,说得对。性子是急了,光想着往前冲,忘了带兵也要有春风化雨的耐心。”他粗粝的手指用力搓了搓额头,仿佛要将那急躁的印记抹去。
王刚的目光随即转向李锐:“李锐,你小子肯钻研,脑子活络。可你那个内务,被子叠得跟‘坦克’似的,棱角全无!小事见精神,这是当兵的样子?”这批评像一阵冷风,吹得李锐耳根瞬间烧得透明,他猛地挺直了腰板,只低低应了一声:“是!班长,您说的对!”
会议室那场深刻的自我剖析与批评,如同一次灵魂的淬火。每一次红脸出汗的刮骨疗毒,每一次并肩协作的会心一笑,都在悄然重塑着筋骨,凝聚着魂魄。高原的风雪可以冻僵岩石,却无法冷却这炉膛里反复锤炼出的信念——那是在党旗团旗下点亮的初心,在一次次真诚的碰撞与温暖的相融中,愈发坚韧如钢。(作者:朱京启、代芯语、柳聪聪)
 会员投稿
会员投稿 手机版
手机版 | 教育频道
| 教育频道